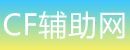- 首页
- CF辅助
- CF河马辅助网,丁乙:漫长的出走高温黄色预警:广东部分地区可达37℃至39℃贵阳灯光秀亮相央视《新闻联播》选拔启动!中国空间站等你来出差两位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上海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另有2例确诊病例被刑事立案侦查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都已停止泄漏10月2日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龙和凤是两口子吗?真相万万没想到.图解生活(21)73张老照片,我们一起见证新中国的发展。俄宪法法院认定顿涅茨克等四地“入俄”条约符合俄宪法超37!这七省,“高温警报”拉响俄罗斯暂停向这一国“供气”俄罗斯暂停向意大利供应天然气俄宪法法院:四地“入俄”条约符合俄宪法明确了!浙江高考,重大变化!
2022 年,艺术家丁乙度过了自己的 60 岁生日,并同时准备着两场展览,一场在拉萨,另一场在青岛。6 — 8 月,两场展览依次开幕。从高原到东部滨海,丁乙几乎将他生涯中所有的绘画作品都展露了一遍。
从画布、粗布到瓦楞纸,从油画颜料到丙烯颜料,从炭条、粉笔、油画棒到圆珠笔,从黑白、彩色再到荧光,从早期的三原色到俯瞰的城市,再到最新创作的喜马拉雅山山顶的白和东海的海天一色,跨度长达 30 余年。
在旁观者看来,这些抽象画作都是艺术家数十年如一日描绘的 " 米 " 字与 " 十 " 字,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冲动,也不会有原教旨主义的压抑,一切来自外部、观念和潮流的风尚在丁乙的画布上都要被他稀释到与原有画面不相冲突的程度,所有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着。只是有的简单如窗布,有的复杂如星空。
然而事实是,在每一个工作阶段,丁乙都试图穷尽当时采用的观念、方法和形式的潜力去与画面决斗。在外部的狂热、绘画的窠臼和自认的陈词滥调中,他不止一次地转变与出走——无论是上世纪 80 年代他决意要做一个 " 形式主义画家 ",还是世纪之交,巨变的城市闯进画布打破了他最初的理想。
从 2010 年开始,丁乙的目光越过了上海——即使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上海画家,在一次与肖恩 · 斯库利的对谈中,他甚至说:" 我不能离开上海,离开上海我会枯萎。" 但丁乙仍然把着眼点放到了人类历史的天空与星辰中。
他频繁地去第三世界国家和自然之地,在哈瓦那感受贫富的差距与世界的多维,在风化数百年的雅丹地貌感受倾斜的魅力。虽然远行与壮游常被视为艺术家感受崇高的方式,但对丁乙来说,那些身体上的先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工作室里才会频频反刍,他所要做的,便是用这些诞生于工业城市的、无意义的 " 十 " 字和 "X" 符号,绘制 " 交代天空与大地秘密 " 的画作,并以此通向精神世界。
" 无限层次的白 "
丁乙已不是第一次去西藏了。1989 年,还处于学生时代的他辛辛苦苦地积攒了一笔钱去西藏,回来又成了 " 无产者 ",换来的是一包包藏香、藏红花等内地少见的俏货,唯独没有下笔画任何东西。他当时还没有想清楚自己的绘画语言。
阔别 20 年后,丁乙回到西藏,从入海口的工业城市到三江之源的土地进行了一场精神寻踪。他先后探访了白居寺、夏鲁寺、萨迦寺和贡嘎曲德寺等西藏壁画遗珍,并于夜幕降临前的 15 分钟抵达了珠峰大本营。
在海拔 5200 米的寂静暗蓝的包围中,丁乙感受到了 " 无限层次的白 " —— " 所有的暗都衬托了珠峰的白——不是阳光下的白,而是有结构的白,无限层次的白。山峰的结构是异样的,有某种无法言说的模样……所有东西都变得次要了。也许是抵达大本营的激动打败了所有东西,当时没有感觉缺氧或不适,夜幕降临,最大的感受就是寂静。脚步都是轻盈的,已经分不清真实和自我判断的边界。不知身在何处,是珠峰脚下,还是在宇宙里。感觉有些悬浮,脑子里好像没有其他日常的任何痕迹。"
丁乙以静谧深邃的蓝色作为绘画的主色调,不断摸索那个傍晚世界最高峰给他带来的震撼。他以此画了七幅珠峰,有纸本色粉,也有木版雕刻,在他笔下的珠峰是运动的,变得如同蓝色夜空中闪烁的银河,起伏的山峦成为绝对抽象的一条白色光带。同样被自然震动的经验也发生在青岛。
在西海美术馆,丁乙透过展厅四扇尺度不一的菱形窗户,窥见东海海天一色的动人景色,并以此创作了一系列全新的作品。日夜晨昏之中不断变化着的天空、海洋与星辰等图景,沉浸于画面上流动的无限。
丁乙不是一个画风景的画家,画作都是在回沪之后创作的,带回的不只是藏纸、矿物颜料等在地的材料,还有自己最在乎的身体感受," 那一刻是感人至深的,会在图像记忆里久久存在 "。就像丁乙喜欢的浓缩咖啡一样,从高原到平原,有一种身体的瘾,不一定是舒畅的,但一定是渴望的。
一个 " 货真价实 " 的上海品牌
在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 · 沃斯(Louis Wirth)提出把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理解后,人们愿意把这种理解凝神在一个人身上。圆形的眼镜、抽象画的都市韵律和艺术家本人钟爱的、带有享乐色彩的美酒与雪茄,让丁乙成为这个人。
策展人侯瀚如评价丁乙是一个 " 货真价实 " 的上海品牌。这不是指丁乙要成为一个与美加净、百雀羚或者凤凰、海鸥一较高低的人,更多是指现代主义的零光片羽散落在中国后," 为艺术而艺术 " 的理念以另一种形式被接续起来。
丁乙画 " 十 " 字的故事被说过很多次了。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装潢设计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至一家玩具厂工作,负责包装的设计。当时,工业流程所要求的精准度依赖于 " 锚点 ",也就是设计中最为广泛使用的辅助标记 " 十字线 "。
两个 " 十字线 " 相连,决定了一段长度;而将 " 十字线 " 向四个方向延伸,又能形成网格,从而进一步确认设计元素的位置。这便是 " 十示 " 系列作品的由来,它只是让绘画更加抽象,没有任何引申义在里面。丁乙在主观上寻找一种新的可能,这种稚拙可以理解为一种 " 为赋新词强说愁 "。
" 十示 " 系列作品的第一幅是红、黄、蓝三原色,第二幅是七色光谱,光洁、平滑,如同一个生涩的宣言,说明从今天开始他要这样画。在此之前的作品《破祭》《禁祭》被认为是丁乙 " 十 " 字的先声,尤其是《禁祭》上面的 " 十 " 字,严格来说更像 "X",一个否定一切的符号。
丁乙这样说:" 我必须把我身上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去掉、中国的绘画传统也去掉——从零开始。" 那是在 1986 年,丁乙的画室条件很差,租金只要 15 元,他自己题了 " 索居 " 两个字。" 当时每根线条都是用丁字尺和鸭嘴笔画出,再把颜料填进去。"
一不小心,丁字尺歪了就会破坏画面。并没有多少人理解他要 " 从塞尚的起点重新走一下 " 的雄心。他几乎天天晚上都在画画,如同所有抽象美术的劳动者一样,他在蒙德里安和弗兰克 · 斯特拉(Frank Stella)的作品中建立起对结构和色彩的理解。
但在这样一种创作里面,丁乙很快又面临了新的困境。作品必须平放在桌面上弯着身子来画,几年工作导致丁乙的腰出了问题,直不起来,所以他必须寻找新的绘画手段来改变这种绘画所带来的身体方面的压力。
" 这个突破口对于我来说是改变为一种‘口语化’的方式。我需要修正所谓精确的概念,寻找其他可能精确的表述语言。人完全放松了,作品同样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于是再也没有微妙的、缠绵悱恻的细节能够束缚他的手脚。
这座城市温情的手工业和早期的机械工业在他的作品中回归。看看那些上世纪 90 年代的物质痕迹吧,木炭画的黑色的叉、杀蟑螂的 " 神奇粉笔 "、教学用的彩色粉笔和裁缝用的扁的画粉,都被丁乙 " 征用 " 过。
他在折叠的扇面和屏风上作画,也在瓦楞纸和包装盒上作画。丁乙还购入现成的花布、格子布,以原有的纹样为基底,通过增添 " 十 " 字或笔触形成 " 画中画 " 的效果。有时,他也强制性地改变格子布原有的基底色彩,在上面呈现他自己的纹样。
因为对黑色反光效果感兴趣,他还通过重复覆盖丙烯颜料,或用铅笔,或用圆珠笔,在画面上制造黑色的反光。那时,丁乙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布店选布。周围人都以为他是做服装设计的,或者是个画花布图案的纺织厂美工,丁乙总为此感到愉悦,因为在最早开始做和 " 十示 " 有关的草图时,他在思想上已经明确了抽象创作的目标和方向:让抽象介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
" 青磷似的绿焰 " 和 " 火一样的赤光 "1998 年,丁乙从郊区搬到城里,拥有了一个 300 平方米的工作室——苏州河西岸边石门二路的一栋两层小建筑,从大门沿着极缓的台阶直接可以上到这里。完整的木结构依然如故,粗大的横梁虽然灰旧了,但还是笔直挺拔的。
建筑是 1921 年英国人设计的一座粮食仓库,极缓的台阶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负重上楼而特设的。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塞吉 · 居尔布特(Serge Guilbaut)的到访影响了丁乙。居尔布特看到当时上海正在经历巨变,但这里的艺术家却都很宁静,在自己的系统里冷静地工作,这种与外部世界的脱节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 上海能让你感觉到最喧嚣的、最繁荣的大都市气息,而你进入(艺术家)工作室的时候,你可能又是被社会遗忘的。" 除了建筑的快速发展之外,上海也是第一个实施灯光工程的城市。整个城市充斥着大量的霓虹灯广告,高架上泛着明亮的灯光,一片炫目。
丁乙在高楼上鸟瞰这个城市时,就能看到那种闪烁的荧光感觉。从 1999 年开始,丁乙在作品中使用荧光和金属的颜色,画出茅盾在《子夜》中形容为 " 火一样的赤光 " 和 " 青磷似的绿焰 " 的上海霓虹灯,一些欲望与失落也在那时进入了画面,比如股票。
抽象绘画是一种城市艺术,在变动的景观中谋求着一种恒定。为了对苏州河沿岸环境进行有效整治,政府以 3000 万元的价格与这里的企业置换了产权,作统一规划。丁乙被通知要在夏天前迁出,这里要被改建为一个绿草如茵的公园。
再找到这样的工作室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海的大小仓库、旧厂房都被丁乙像过筛子一样一一筛过,十几年来,丁乙辗转于 M50 园区、西岸,今年又临时到了青浦,城市肌理消弭的过程,如同河里的一副鱼脊显露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的搬离与出走,自然也有这座城市几分潜流、野史和手册的味道。
丁乙尝试过画一个无光或者少光的上海。1982 年,丁乙在莫里斯 · 于特里约的城市风景画的影响下进行创作,他到老街小巷里写生,身临其境地比对、画画。于特里约笔下的巴黎是一个充斥着灰色厚度的城市。
冷清的街道,描绘在奶白色、牡蛎白、暖灰、橄榄色和蓝灰的微妙和谐之中,再加上浓黑和棕色造成强烈对比。丁乙喜欢在此基础上画房屋的窗框和洋房的铁篱笆。他钟情于那些装饰,那些简单的符号早早地表明了一种热衷于抽象的气质。
踏入同一条河流近几年,丁乙隐约地感觉自己在寻找一种新的社会精神,但很难定义,无法捉摸。不过,丁乙在绘画上自始至终相信时间的力量,劳作的叠加会换来天道酬勤。不分南北,遑论东西,现在的丁乙已经不想谈那些有关艺术本体论的东西了。
一次又一次的出走,造就的是一个又一个陈旧的词。他感受到紧迫,感受到宏观之于抽象的必要,但他的应对方式又如此传统——在家中仅剩的一本速写本和两本藏纸册页上画画,画坠落在夜色中的上海,画他每日希望记下的东西。
好在丁乙习惯了于限制中创作。在使用荧光色绘画的阶段,他常用荧光绿,其余的就是荧光黄、荧光橘红和荧光桃红,12 年间就是在四种颜色的基调里面进行工作的,面对限制进行各种突破。"(绘画)不在于一种最丰富的描述,描述语言里有很多本质的东西是不变的,可以延展到绘画的很深处,它代表着某种力量,可以非常持久。"
在荧光色损害他的视力之后,他又创作了一批以黑白色为主的画作。从 2019 年开始,丁乙时常觉得自己回到了 1991 年。他会在工作室挂起 1991 年的作品——那个时候在两个板凳之间铺着画布,用尺一点点演进;那时还没有展览,没有艺术市场,也没有参观者登门,就是为了某种年少气盛的盲目理想。
" 有时候我一天画下来,感觉自己这个方式很像传统的画家,虽然脑子在转,但行为方式很传统,花大量时间融在创作里面。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我的灵感之源就是这些工作本身。每一张作品的变化都是跟前一张未能完成的东西有关。也就是说,当完成了一张画之后,我就会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当一张画没有完成的时候,它也会生成对下一张画的作用。"
" 一件作品要经得起看、让观众看不完 ",同时需要激起某种共鸣,为这个时代留下某种印记,然而这谈何容易。丁乙在一张张画上推演、盘算,这周而复始、永不止息的劳作,像不断地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可能就是他与绘画的终生决斗。
- 系列
- 视频
- 充气
- 怎么
- 大全
- 游戏
- 民警
- 代理
- 平台
- 活动
- 论坛
- 回复
- 即可
- 火线
- 求生
- 这一
- 电脑
- 永久
- 开发
- 但是
- 不过
- 制版
- 危机
- 生化
- 修改
- 可以
- 金山
- 功能
- 辅助
- 熊猫
- 刺激
- 战场
- 钻石
- 软件
- 销售
- 武器
- 介绍
- 地铁
- 一次
- 付费
- 订阅
- 服务
- 消费者
- 个人
- 喜欢
- 苍穹
- 安装
- 管理
- 角色
- 速度
- 女性
- 跳跃
- 设置
- 点击
- be
- 美元
- 目标
- 评级
- 名单
- 最佳
- 3月
- 更新
- 麒麟
- 英雄
- 联盟
- 手机
- 智能
- 皮肤
- 图片
- 方面
- 同时
- 习惯
- 透视
- 枪战
- 穿越
- 战争
- 战略
- 即时
- 系统
- 目前
- 作弊
- 也是
- 节奏
- 各种
- 不得不
- 道歉
- 犯罪
- 科技
- 获得
- 模式
- 购买
- 周年
- 发动机
- 搭载
- 交易
- 手续费
- 方式
- Be
- 当中
- 直播
- 打开
- 工具
- 还是
- 版本
- 突围
- 知道
- 指定
- 大师
- 医院
- 核酸
- 阴性
- 价格
- 这个
- 来说
- 时候
- 工作
- 越南
- 真的
- 骑着
- 技能
- 守约
- 百里
- 神秘
- 任务
- 一个
- 官方
- 资源
- 篮子
- 对方
- 非常
- 存储
- 容量
- 大伙儿
- 热血
- 地图
- 装备
- 融合
- 进行
- 物资
- 答题
- 比赛
- 甚至
- 一场
- 布朗
- 球队
- 志愿
- 填报
- 免费
- 中原
- 规划
- 数据
- 通过
- 引擎
- 认证
- 计划
- 封锁
- 全境
- 时间
- 吉利
- 物质
- 手榴弹
- 黑市
- 控制
- 配置
- 落地
- 弊端
- 美化
- 行为
- 程序
- 还有
- 旅店
- 报道
- 收购
- 信号
- 竞技
- 如何
- 里面
- 机油
- 合成
- 使用
- 表彰
- 碎片
- 阴阳
- 赠送
- 名片
- 决赛
- 炸弹
- 大家
- 攻击
- 那么
- 他们
- 自己
- 用户
- 赛事
- 记者
- 先生
- 先锋
- 机枪
- 吹风
- 高速
- 头发
- 分钟
- 工业
- 模具
- 加工
- 术语
- 火车
- 这里
- 已经
- 信息系统
- 计算机
- 或者
- 非法
- 幽灵
- 关卡
- 幻想
- 最终
- 日本
- 性别
- 平等
- 合作
- 显示器
- 面板
- 成为
- 前来
- 庆典
- 不服输
- 论文
- 网站
- 写作
- 子弹
- 木雕
- 雕刻
- 作品
- 手工
- 中国
- 问题
- 大部分
- and
- 模拟
- 练习
- 视野
- 敌方
- 公司
- 操作
- 给你
- 学生
- 职业
- 技术
- 脚本
- 冲突
- 领取
- 黄金
- 奶妈
- 遇到
- 开启
- 处理
- 性能
- 高性能
- 转移
- 这样
- 商洛
- 歌曲
- 创作
- 音乐
- 逃生
- 城市
- 包含
- 转为
- 转换
- 文字
- 机器
- 成功
- 剧情
- 挑战
- 推荐
- 终结
- 太极
- 帝国
- 重返
- 行军
- 题材
- 就是
- 金融
- 能力
- 研究
- 低价
- 入手
- 发布
- dOS
- 超人
- 电影
- 宣传
- 什么
- 沙漠
- 僵尸
- 泡泡
- 梦幻
- 发现
- 超级
- 最后
- 鼠标
- 笔记本
- 现在
- 开火
- 瞄准
- ??
- in
- 数码
- 驱动
- 配色
- 火箭
- 连胜
- 三分
- 拾取
- 自动
- 这时候
- 你的
- 如果
- 运营
- 支付
- 移动
- 统筹
- 互助
- 车辆
- 业务
- 陷阱
- 伤害
- 银行
- 信用卡
- 联网
- 主机
- 奖励
- 裂缝
- 激光
- 背包
- 强化
- 设计
- 谣言
- 骗子
- 出现
- 朋友
- 近期
- 方法
- 箱子
- 巴掌
- 方向
- 队友
- 对面
- 我的
- 延迟
- 这种
- 我们
- 邮箱
- 隐藏
- 世界
- 下载
- 也就是
- 很多
- 内容
- 权益
- 本身
- 飞机
- 小学生
- 都是
- ID
- 战地
- 小说
- 爆竹
- 许可证
- 数字
- 无限
- 中的
- 叛乱
- 教材
- 突破
- 打击
- 交易所
- 商人
- 飞船
- 买卖
- 进去
- 测试
- 能够
- 开放
- 帐号
- 加速
- 验证
- 妹子
- 死神
- 人员
- 框架
- 加速器
- 进入
- 主角
- 无敌
- 完结
- 医疗
- 不要
- 检测
- 所以
- 取暖
- 欧洲
- 咱们
- 扫射
- 屏幕
- 管道
- 立即
- 焊接
- 密封
- 文件
- 压缩
- 搜索
- 历史
- 故居
- 习近平
- 建筑
- 电视台
- 撤离
- 保险
- 企业
- 护士
- 他的
- 手柄
- 迷雾
- 宝贝
- 疯狂
- 身上
- 关于
- 动轮
- 复活
- 切换
- 频道
- 国产
- 因为
- 这么
- 头条
- 编辑
- ME
- 文本
- 采购
- 项目
- 提供
- 射击
- 完成
- 改造
- 升级
- 东莞
- 男人
- 没有
- 预选赛
- 登录
- 葡萄
- 工人
- 机器人
- 苹果
- 唯一
- 上海
- 故事